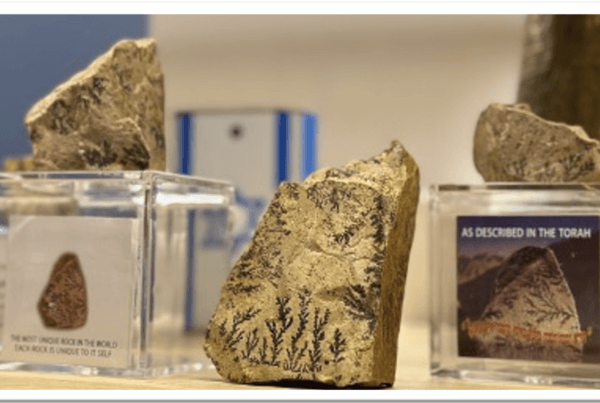從透過粗厚羊皮卷軸上精心雋刻的字母傳承妥拉的時代,到現在只要用手指輕觸超連結,就能立即在智慧型手機上閱讀妥拉的某個段落,數千年來,文字幾乎是猶太人與妥拉故事互動的唯一方式。少了圖像的輔助,讀者只能仰賴想像力,讓妥拉中的故事情節躍然紙上。

Mauricio Avayu
數年前,猶太裔智利藝術家 Mauricio Avayu 開始著手改變這項千年慣例。在花費數年時間專注打磨畫技,並於拉比的教導下經歷密集的個人化研究課程後,Avayu 便全心投入繪畫領域,在他的妙筆之下,妥拉的故事情節與人物在一系列彩色壁畫中鮮活展現。
自開始作畫以來,Avayu 已收到來自多位拉丁美洲國家前任元首的創作委託,並在美洲各地的著名藝廊展出作品。最近,他將心力放在一組三幅,高達 2 公尺,描繪《創世紀》場景的壁畫上。這些畫作係由薛智偉猶太社區中心委託繪製,並將永久展示在中心內,該中心預定在 2021 年底於台北市中心開幕。社區中心為薛智偉坣娜猶台文化交流協會 (JTCA) 的旗艦計劃,該協會是近期成立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在台灣和全球各地推廣猶太生活、文化和律法奉行。
最近,Avayu 透過 Zoom 與 JTCA的 全球溝通總監 Glenn Leibowitz 對談。在他位於佛州阿文圖拉市的工作室,Avayu 向我們娓娓道來,說明他如何轉化畫壇大師對他的嚴格訓練,並利用屬於自己的日常儀式釋放創作力,將妥拉的故事和象徵以繪畫方式生動地呈現在我們眼前。此外,Avayu 也在訪談中解釋為何他相信自己的藝術能應對反猶太主義的興起。為求簡潔明瞭,以下談話經少許編輯。
是什麼啟發了您繪製妥拉故事的想法呢?
由於熱愛魔法等神奇的力量,我一開始是描繪神話故事。然而有一天,我的心苗突然乾涸,靈感不再泉湧。我發覺到自己得向更深處邁進才行。當時我正在讀有關米開朗基羅的書,並到西斯汀教堂細細審視了他壁畫中的各項細節。壁畫的主題是亞當、夏娃與蛇,但我看得出來,米開朗基羅在畫中敘述的故事是錯誤的。
西斯汀教堂裡的蛇盤繞著分別善惡樹。但既然聖經中對蛇的懲罰是終身匍匐於地,這樣畫就不對了。改變故事就是改變聖經、改變妥拉,這是不行的。
因為米開朗基羅,所有人都認為神是用手指賦予了亞當生命,他的畫作為大眾帶來這個熟悉的印象。但其實神是以呼吸賦予亞當生命,而非手指。此外,米開朗基羅也將一些希臘神話故事和新約聖經的故事混雜在一起呈現。舉例而言,大家都認為伊甸園的禁忌之果是蘋果,但實際上卻是無花果。這正是讓我下定決心要把妥拉畫出來的原因。我以為,如果我用 Google 搜尋,應該會找到一大堆妥拉壁畫。但令人驚訝的是,我居然找不到之前有任何人曾畫過妥拉。那是因為畫家必須雙管齊下,不只要擁有繪畫技巧,更要了解如何研究妥拉。有些人致力於研究,而另一些人則是專精於繪畫,但我得兩者皆精才行。
我太太問我:「為什麼要畫妥拉,你又不懂」,我跟她說,這有兩種解決方案,不是別畫壁畫,直接放棄,就是開始研究妥拉。於是,我決定開始學習猶太經典。
我去了可巴德,並告訴那裡的拉比我什麼都不懂,需要他協助我學習。拉比對我說:「好,每週二我都會待在這裡一個小時,你可以趁這個時候來問我任何你需要知道的事。從此我便每週去找拉比。我有一本英文版妥拉的西班牙文譯本,由 Aryeh Kaplan 翻譯,品質非常優秀,於是我也開始閱讀妥拉。那本書中沒有任何評論,但譯文極為精準,對當時不太懂希伯來文的我而言幫助很大,讓我對妥拉有了基本的認識。
然而,我後來發現自己並未真正理解妥拉。因為若只是接受妥拉表面上的意義,你便無法徹底明白其根本意義所在。因此,我得讀更多的書。我接觸了米德什拉 (Midrash) 的故事以及註經家拉什(Rashi) 對妥拉的評論。
除了教您妥拉之外,拉比還有針對您的畫作提供任何指導嗎?
有次我在畫畫時,腦中浮現了一個圖像,由於不想畫出被禁止的事物,我便請拉比過來看看。我在畫亞伯和該隱時,突然很想畫亞伯的羊。我想在牠頭上畫兩支角,就像羊角號 (shofar,一種樂器) 那樣。
「我想把這個地方畫對,這有被禁止嗎?」我問道。拉比告訴我:「你必定是在米德拉什中讀到這個的吧?」但我沒有讀過任何這樣的場景,我只是凴感覺而已,我將此事告訴拉比,他對我說道:「不對,不可能只是感覺到。米德拉什上有記載,說彌賽亞將吹響亞伯之羊的羊角號」。
這種現象在壁畫裡、在我的畫作中處處可見。就像有另一個聲音指示我把某個東西畫在這、那邊要如此處理、這兒得要修改一下之類的。有時,你會把整週都耗費在畫某樣東西上,但當你回神一看,發現畫得很糟,你就得把它擦掉。有時你會感覺得心應手,一週的時間飛快流逝,就好像只過了一天般。藝術學校的科班訓練,是要我們試著重現在照片中看到的事物,而我則依循另一種方法,站在畫布前,用心感受。
顯然,我需要先讀過妥拉,對故事內容有所了解才行。我並不想竄改故事,但出現在畫布上的形狀、比例和事物,都不是預先設計好的,我稱其為「神聖的意外」。剛開始作畫時,壁畫就像個神祕的謎團,直到畫完,你才會恍然了悟它所呈現的樣貌。
我在閱讀時,腦中會浮現電影般的圖像。作畫時,我便下筆重現出閱讀時腦中呈現的影像。我不太打草稿,通常只是把畫布往牆上一掛,直接開始作畫,甚至在下筆之前,我就已經知道成品的樣子了。
你在繪畫中融入卡巴拉象徵主義 (Kabbalistic symbolism) 和妥拉中隱微的訊息。大家對此的反應如何?
現在人們已經習慣在我的畫裡找來找去。研究卡巴拉多年,我曾經在畫中置入許多卡巴拉的思想。為何亞伯拉罕持杖時,右手蓋在左手上呢?因為亞伯拉罕與慈愛 (chesed,仁慈) 有連結,而這個概念又和右側有關,由此可知每項細節都其來有自。解釋原由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便將來龍去脈都呈現在壁畫中。我可以就單一片段講上一小時,說明當中所有細節在妥拉和在米德哈什中代表的意義。這不單純只是繪畫,而是我們猶太民族傳統的故事。我們擁有廣博的知識和資訊,必須和所有人分享,這就是為什麼展覽的名稱叫做「創世紀背後的光」。當你閱讀文字,字面上的意義只是第一層。而愈趨深入,你便會發現更多訊息。一旦開始深入探索,就會想要知道更多。
請讓我們看一眼您的工作室。您在作畫時有什麼例行公事和儀式嗎?
我早上很早就會到工作室,點起肉桂蘋果薰香,放些輕音樂,有時也許來點巴洛克風格。然後我會查看前一天的進度。在長時間工作,漫長的一天即將結束時,你只能看到真實的一部份。隔天,在好好睡過一覺且精神百倍的早晨,你可能會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所以,我會在此時決定要做些什麼,然後重新開始工作。
 我的工作室裡有很多未完成的作品。當我對作畫感到厭倦時,我會做其他事。我想畫就畫,需要上色就上色。
我的工作室裡有很多未完成的作品。當我對作畫感到厭倦時,我會做其他事。我想畫就畫,需要上色就上色。
我讀過一本有關達文西的書,描述他和米開朗基羅之間激烈的競爭。他們絕非朋友,米開朗基羅是雕塑的擁護者,達文西則是繪畫派,因為我們所談論的、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可以融入繪畫之中。若有需要修改的細節,我隨時都能修改。這是我的世界。在這裡,我無比自由。
我非常快樂,充滿感恩。我享受畫畫的美好時光。悲傷時,我無法作畫,煩惱或難過時也不行。我只想把我的能量轉化為快樂和希望,而不想看到畫布上有悲傷的痕跡。
您在知名藝廊辦過展覽,還被兩位拉丁美洲的前任總統親自邀請出展。一開始,您的作品是如何被發掘的呢?
當初我在智利的工作室繪製這幅壁畫時,我常常在想,誰會想看這個?誰會想買?沒有人嘛!因為它只是我自身感受的呈現。然而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猶太社群主席的電話,他對我說:「Mauricio,我們希望你替智利前總統巴舍萊女士 (Michelle Bachelet) 畫一幅畫。我會把你的壁畫帶去總統府。」什麼?你要把我的壁畫帶去總統府?

Mauricio Avayu和智利前總統巴舍萊
我告訴他,這只是我的私人創作,但他卻鼓勵我:「別這麼說,拜託試試看吧」。而後在展覽會上,每個人都為我的畫作起立鼓掌。智利的反猶太主義相當猖獗,因此在展出妥拉時,我感到非常害怕。在總統面前展示妥拉,這一點都不尋常;妥拉可是初次像這樣被展示出來。這也是為何我要納入文字,我不想背離妥拉卷軸,希望卷軸就在畫中。當你注視著卷軸,注視著妥拉捲軸,若不懂得怎麼讀、不明白它說了什麼,那你將會錯過很多訊息。我以妥拉抄寫員 (sofer) 使用的傳統方式寫下文字,並將它和圖像混合在一起。我不用新式印刷術,而是用寫的,就像載於妥拉卷軸中的文字那樣。
至於我在智利的展覽,位於聖地牙哥的新貝內以色列猶太教堂請我繪製亞伯拉罕與瑪拉基姆 (malachim,意為天使、信使) 的故事。所以我畫了兩頭獅子,牠們展開了一部巨大的妥拉卷軸,身旁站著亞伯拉罕和瑪拉基姆。我畫了妥拉的第一和最後一段,總共 42 行。這是項大工程。當我把這些拿給可巴德的拉比看時,他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並允許我這麼做,只要對「yud-hei-vav-hei」一字做些微改變,避免寫出神的名諱即可。之後,我在墨西哥展出壁畫時,那裡的拉比問我:「抄寫員 (sofer) 是誰 ?」我說是我。「不對。抄寫員到底是誰?」他又問了一次,我也再次告訴他,就是我。而他不屈不撓地再次問道:「你不懂我在說什麼嗎?這是誰寫的?」我大聲答道:「是我!」。
我不是抄寫員,但我能看到文字的形狀,我只懂一半的字母,不過,我就是能感覺到輪廓。
早期您還有在哪些地方展出作品呢?
有一天在工作室裡,我接到一通墨西哥迪亞哥・里維拉美術館館長打來的電話,美術館之名取自全球最重要的壁畫家之一。那瞬間,我覺得這是開玩笑的吧!一定是朋友在跟我惡作劇,假裝自己是迪亞哥・里維拉美術館的館長,並要在他的美術館裡展出我的壁畫。但仔細一聽,就能聽出他的確是墨西哥人,我隨即意識到這不是開玩笑,而是認真的。他跟我說:「我們想在 9 月展出你的壁畫,現在告訴我,行還是不行?」我當然回答「好」囉!

Mauricio Avayu 與墨西哥前總統Vicente Fox和其妻
當時,我正在處理三個非常大型的委託創作。我對他說,我的時間已經排滿了,根本沒空做這個,其實是不可能接下這個工作的。不過,那是妥拉第一次在迪亞哥・里維拉美術館亮相,這是我決定應邀出展的唯一原因。
那是我第一次在智利以外的地方設展,所以我很難拒絕。之後我開始了朝六晚十二的日子,每天只睡四到六小時,大概持續了七到八個月之久。我帶著壁畫前往墨西哥,一路來到墨西哥市的西奈・塞法迪山 (Mt. Sinai Sephardi) 社區。然後我便接到了墨西哥前總統比森特·福克斯的電話。他對我說:「我非常喜歡你的作品」。
人們對你的作品反應如何?
第一次展出時,看到很多人對著壁畫哭泣,我感到非常驚訝。發生了什麼事?也許我做錯了,我不想傷害任何人。為什麼他們在哭呢?初次展出期間,我看到一位老先生在大天使伽百略前哭泣。我以為我犯了什麼錯誤。老先生年約 80 歲,不斷啜泣著。我拿了杯飲料給他,問他怎麼了。他說他的一個孫子因意外過世,而孫子的名字就叫伽百略。
 他看到畫時,鯁在喉嚨裡的一個大結突然鬆了開來。他開始大哭,那是他療癒的方法。他抱了抱我就離開了。稍後,畫廊經理過來跟我說:「你知道那個人是誰嗎?他是全世界的重量級律師之一,為好幾家全球大型公司處理官司」。這個經驗讓我了解到,你的身份根本無關緊要,站在畫作前,就是會像個孩子一般情感潰堤,這就是用心作畫的力量。
他看到畫時,鯁在喉嚨裡的一個大結突然鬆了開來。他開始大哭,那是他療癒的方法。他抱了抱我就離開了。稍後,畫廊經理過來跟我說:「你知道那個人是誰嗎?他是全世界的重量級律師之一,為好幾家全球大型公司處理官司」。這個經驗讓我了解到,你的身份根本無關緊要,站在畫作前,就是會像個孩子一般情感潰堤,這就是用心作畫的力量。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女士注視著以撒和雅各的畫像。那是我最初幾次展出這幅畫,當時我才剛開始下筆沒多久,畫中場景是眼盲的以撒正在祝福雅各,而他以為接受祝福的人是以掃。我看到那位女士在哭泣,便問她怎麼了。她答道:「我父親過世時眼睛看不見。那就是我父親」。
昨天,我和美國某重量級畫廊簽約。他們在紐約、邁阿密和杜拜都有開設畫廊。經理來到我車庫裡的工作室,告訴我他完全被這些畫征服。他說我的作品「令人屏息」,還問我:「這些年你都躲去哪了?」
您的簽名有什麼意義嗎?
我的簽名是「Mavayu」。「M」代表我的名字Mauricio。 而你應該可以看出「y」是希伯來字母的「shin」,跟門框經文盒上的 shin 是一樣的。「Shin」代表「全能 (Shaddai)」,是神的其中一個名字。組成「shaddai (全能)」一字的希伯來字母為 shin、dalet、yud,其中包含一個密碼。「Shin」代表「shomer」,意思是「保護」;「Dalet」表示「delet」,意為「門」;而「yud」則是「以色列 (Israel)」的第一個字母。組合起來,「shomer-delet-Israel 」的意思便是「以色列之門的守護者」。想像一下有多少細節可以藏在畫裡。萬事萬物皆有跡可循,絕非意外出現。
我習慣在畫作上使用很小的簽名,因為我認為,這些畫作並非我自己獨立完成,我只是它的一部份罷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會說「簽名大,畫作就小;簽名小,畫作就大」,我把這句話奉為圭臬。把名字簽小,是因為我們都需要抱持謙卑的態度。不只我的畫,很多人都致力於這點。
真正的重點,是神說了什麼,以及畫作要和世人分享的訊息。我畫畫不是為了出名、不是為了成為世界上最知名的畫家而名留青史,而是為我自己、為這個世界而畫。
你是何時決定要成為專業畫家的?
多年前,我在電視上看到我未來的老師。我立刻感受到,總有一天,他會告訴我:「你一定要成為藝術家,一定要每天作畫才行。」那時我幾乎無法和他聯絡,當時沒有網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他。又過了 20 年,我才初次見到他本人,而當下我驚慌無比,畢竟 20 年前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個人就在眼前。我問他有沒有授課,他回答:「有,你來上課吧」。在第一堂課中,他就告訴我:「你是個藝術家。在另一世,你是才華洋溢的畫家。我沒辦法教你什麼,我只需要幫助你回想起你早已知道的東西,沒有別的了」。從那天起,我便了解到我是個藝術家,前世我更當了一輩子的畫家。向老師學畫時,我並不想以業餘愛好者的身分執筆。我想要習得高超的技巧,讓我能向全世界展現我的藝術。
當時你幾歲?
接近 40 歲。40 是個很重要的數字,是邁入初老的年紀。以色列人在沙漠裡流浪了 40 年之久;諾亞在方舟上時下了 40 天的雨;摩西則花了 40 天取得神的律法。
字母 dalet 代表的數值是四,在卡巴拉哲學中,不管 dalet 或 delet,其實都是一樣的,因為它們擁有相同的數值。所以 dalet 等同於 delet,都代表「門」的意思。這就是為什麼我的門在 40 歲時才打開。40 歲時,改變可以來得非常迅速,那是因為我們明白自己的時間所剩無多。我知道,是時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很多人都在 40 歲時迎來人生轉折,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年紀。我在 2012 年舉辦第一個畫展,其後的 8 年間,我又辦了快 30 場畫展,這是相當龐大的數字,需要投注很多心血準備。
跟您的老師學習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師從 Hernan Valdovinos,他是一位在佛羅倫斯學習的畫家。每週二早上 10 點到下午 1 點間,我都會去找他上課,學了快 9 年的時間。有時候是 10 點半開始上課,有一次我早了 5 分鐘,10:25 分就到了,我便先敲敲門,他開門問我現在幾點,我回答 10 點 25 分,結果他竟當著我的面就把門關起來了。
他就像個軍官一般,極為嚴格,我們曾經用鉛筆畫了三個月的直線。我在 2006 年時就意識到自己並沒有太多時間,而我需要對的老師。不過,我立刻便明白,若想在繪畫方面出類拔萃,就需要這麼做;若想攀上頂峰,我得在學飛之前,先學會怎麼走路。人們問我:「你是怎麼做到的?」那是因為我在嚴師門下習藝九年之久。
老師握了握我的手,並說了兩個令我永誌不忘的事箴言。他說作畫時要像個孩童一般,試著回想起孩提時代所體驗到的感受,跪在地上,精力旺盛地作畫時那種快樂的感覺。但你也必須結合孩童的活力和繪畫的卓越性,你沒法向孩子要求「卓越」這種東西。
數年之後,我了解到,繪畫的秘密,就是畫裡的每項細節都必須追求卓越性,即使不是最重要的細節也一樣。例如,有一幅亞伯拉罕的畫,背景是巴比倫城,畫裡可能有 100 扇窗戶,而每扇窗的反射光線都需一一呈現。當然,窗戶並不是畫中的主角,亞伯拉罕才是,但畫裡的每個細節都必須臻於卓越,若非如此,畫就不算完成。
我致力於追求卓越。我的生活很悠閒、放鬆,但在工作室裡,我一點都不鬆懈。反而非常有紀律。
您曾經說過,您的畫作能應對全球反猶太主義的興起。為何您會這麼認為?
促使我作畫的另一個原因,是世界上沒有猶太人畫過妥拉壁畫。這是為什麼呢?我們明明有許多資訊要分享;義人 (tsaddikim) 的故事被口筆傳頌多年,那為何不能把這些故事畫給人們看,告訴他們:「這些是我們的族人」呢?我們必須向世人分享這些。
反猶太主義源於恐懼。當人們明白所有人其實都非常親近,人與人之間差距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大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抵擋反猶太主義的侵門踏戶。妥拉裡的某些故事,是我們與基督徒和穆斯林共有的,我們擁有相同的根源。
我曾替 14 位福音派牧師籌備過一場特展。其中一位哭著告訴我:「謝謝你。我以為我懂,但其實我並不懂。現在我知道更多事了。」
您正在為台灣薛智偉猶太社區中心繪製壁畫組,請多告訴我們一些相關資訊。
這組為台北猶太社群所繪製的壁畫,和從智利總統巴舍萊處送到當時人在墨西哥市西奈・塞法迪山中心的墨西哥總統比森特·福克斯手上,而後落腳於迪亞哥・里維拉美術館的畫作是一樣的。在高度講究細節的初始繪圖上,我又塗了數層油彩。所以,可能你某天看到這幅畫,過了幾個禮拜樣子又不同了。畫還是同一幅畫,但上了新色層。現在這幅畫作已可展示,我希望能親自到場說明畫中的涵義。
壁畫能飄洋過海來到台北,實在太不可思議了,就好像做夢一般。我非常開心,當這幅壁畫展示在台北的猶太社區中心時,會有很多人看到;如此一來,它就不再只是一幅放在私人寓所裡的壁畫,這就是我們有義務在世界各處發揚的光明。
您預計要花多久時間完成以摩西五書為基礎的彩繪壁畫?
我不知道自己要花多少年才能完成,但這是終生的志業。我目前在畫出埃及記,或許這幅壁畫的某些部分會送到台北,而我也可能需要再重新繪製。重畫時,壁畫的樣貌會有些不同,身為藝術家,我今天畫的可能和其他時候畫的不一樣,我每天都在成長。